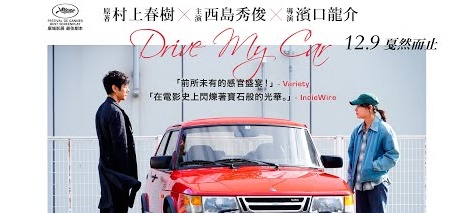電影《哈納萊伊灣》的儀式感―以愛之名,我還想念你嗎? /蔡雨杉
- 專題內容
- 嚴選好物
1.疫情中的儀式感
遠距上班中,漸漸喪失時間感,連出門也自肅,在三級警戒下,與日曆上的日子,漸行漸遠。一周一次的採買,有種村上筆下人物的既視感,發現為自己做個小黃瓜三明治,深坐在沙發上追劇,竟然是我最幸福的儀式感。
托宅在家工作(WFH)的福,終於有機會看了電影《哈納萊伊灣》。電影描寫一個喪子的母親,十年來沒有流過淚,卻年年重訪兒子過世的可愛島(kauai或譯為考艾島)。實力派演員吉田羊,詮釋這樣一位情緒內斂的母親,挖掘失落的幽微心理,像海潮浪擊般,穩定而有力。我想是一部頗能重現村上文學氛圍的改編電影。
改編自《東京奇譚集》同名短篇(中譯為〈哈那雷灣〉),卻省去許多小說中女主角的獨白和生活背景描述,電影更凸顯她神秘的經歷,及異於常人的反應。為何見了兒子屍體不流淚?為何讓社福團體拓印死者手印,卻拒絕收下?(以下涉及劇透,慎入)

2.以愛之名,我還想念你嗎?
吉田羊所飾演的女主角,在小說中叫Sachi,漢字通常可以寫作幸福的「幸」。Sachi的丈夫吸毒外遇、獨生子夭折的遭遇,令人感到村上伯的命名,有某種蓄意的對比。舞台設在夏威夷的「可愛島」,也迴響著相同氣味。
偶像團體「放浪新世代」的佐野玲於飾演的兒子,在生前和Sachi的親子關係冷漠,依賴Sachi過活,卻不貼心。Sachi不能理解為何他熱愛衝浪?為何還帶著可惡丈夫的紅色隨身聽?
喪子之後,Sachi可以說是花了十年在問自己這些問題。在第十個年頭,近乎絕望的那些摩擦、無法溝通的回憶閃現,或許不只是紅色隨身聽,令她想起吸毒丈夫的家暴與劈腿,或許就連浪遊不羈的兒子本人,都讓他想起自己的婚姻不幸。終於十年後,她不得不承認,「以恨之名,我想念你」。 但當她終於接受這點,主動跟社福團體的女性說,「我恨我兒子,也愛我兒子」,她才終於贖回她的手印,和她的真實感情!

所有的失落,都需要歷經自問自答的儀式,才能找到出口。最重要的是,她沒有一開始就隨俗地,以愛之名哭訴,「我那麼愛你,你怎麼可以離我而去?」,也沒有壓抑她對兒子,其實又愛又恨的複雜心緒。反而是建立了儀式感,十年來靜靜與「海」對坐,細細咀嚼她與兒子的情感糾葛,等待踏實感到能好好告別的時刻到來,她終於敢說出「我想念你」。這是著實是她的儀式感的勝利。


而啟動這個儀式感的,就是村上虹郎所飾演的學生衝浪客。他故意裝作聽不懂英文,親近並仰賴Sachi的照顧;又在聽懂美國大兵貶低Sachi的悲傷不如自己失去許多軍中同袍時,不惜以小搏大,為Sachi爭一口氣(悲傷何能相比);又或者拿起筆記悉數記下Sachi的泡妞建議。他恣意奔放的熱血胴體之下,有著超齡的成熟。種種互動,都與兒子的漫不經心,形成對比;彌補了Sachi作為母親的缺憾,讓她終於敞開心房,讓情緒開始流動。

3. 村上春樹的夏威夷經歷,或者說是有意義的巧合
看這部電影有幾項「非常村上」的小道具和電影主旨相互烘托,例如,Sachi讀的書是,村上愛讀的美國小說家費茲傑羅(F. Scott Fitzgerald)的《人間天堂(This Side of Paradise)》,寓示可愛島自然風光;彈的鋼琴曲是,Giovanni Martini 〈愛情的喜悅(Plaisir d'Amour)〉、George Gershwin〈 I've Got Rhythm〉,盡顯度假地的愉悅氣息。而電影最後才終於揭曉隨身聽播放的是Iggy Pop的 〈The Passenger〉這首歌,饒富趣味,更加深電影的底蘊。
I am a passenger
And I ride and I ride
I ride through the city's backsides
I see the stars come out of the sky
Yeah, they're bright in a hollow sky
You know it looks so good tonight
I am the passenger
歌詞唱誦的是,或許可以理解為導演松永大司下的註解,「光陰者,百代之過客」,但人生在世,仍當喜悅。當Sachi 決意拿起隨身聽,不僅是試著靠近兒子和丈夫的轉變;也暗示了她已經可以接受「死是生的一部份」的心境。過客們,方生方死,又愛又恨,而過客終究回歸自然。當我們接納了這個前提,旅途中,永遠不缺少坦然的笑容。


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還有3個巧合,其一是,村上在2021年5月22日TOKYO FM「村上Radio」的特別節目「用音樂迎接美好的明天」中,為了鼓舞大家在疫情中,相信人生還是有好運。介紹了一個關於他意外獲得Bob Marley《自然主義》的趣聞。他說:「在夏威夷租車的時候,發現Bob Marley 的專輯《自然主義》(Natural Mystic)這張CD留在了汽車的音響裡面。因為還車時,沒有人認領,就把它帶回家了。」後來他在檀香山的商店,看到了出售《自然主義》的二手CD盒和歌詞本。他認為就是原來CD主人出讓的。並總結說:「人生的際遇不可思議,永遠要相信生活裡的好運。」我認為這同時也是他對同樣《哈納萊伊灣》中,Sachi遇到村上虹郎飾演的衝浪客,所下的註解。

第二個巧合是,Sachi喪子,我喪母。我曾寫過悼念的文章〈回收再利用〉。因為母親生前簽署了大體捐贈,因此我馬上就用「不要恨這座島,他只是回到大自然的循環而已」的邏輯,壓抑了我的思念。但朋友看了,覺得我以第三人稱的書寫,並未揭露自己真實情緒,一如Sachi。十多年後,與這部電影兩相對照,才發現原來真正的放下,從來不是一次到位,而是這反反覆覆地試著與悲傷和失落共處時,不知不覺能隨順情緒起伏的坦然,一如衝浪。
第三個巧合是,我曾在擔任講師的日文翻譯課程上,與畢業班學生,一起讀過《村上收音機》。其中,寫他駕車可愛島的散文,〈談談說再見(さよならを言うことは),村上說:「20世紀最後一次除夕,我在夏威夷可愛島(Kauai)的北岸,夕陽非常燦爛美麗。鮮豔的橘紅色塊狀,正要落入山頭時,雲和海也染成相同的橘紅色。我爲了眺望落日而漫無目的地開著車子。收音機正巧播著布萊恩•威爾森(Brian Wilson)的名曲〈Caroline, No〉。聽著之間心頭忽然一陣熱起來,有一會兒說不出話來。……可是在聽著那首歌之間,卻自然而然地升起「我現在就這樣,正在跟時間的一大塊告別著啊」,這樣的心情一點一點地傳遍全身。」(引自賴明珠譯,時報,2012,208頁),並表示這是他少數能夠好好道別的一次經驗。我想這也是村上伯透過《哈納萊伊灣》,想傳達的訊息。

電影的末尾Sachi終於笑了,不知是否她終於瞧見了亡兒的魂魄?抑或是她終於能感到被可愛島所擁抱?但總之,一定是一次好好告別的坦然。片尾響起〈The Passenger〉的時候,在腦海中,我竟然已經經歷了這麼多榮格所說的「有意義的巧合(meaningful coincidence)」!榮格曾解釋道,非因果性之兩者的聯繫,其決定性因素是「意義」,而這是來自個人的主觀經驗。因此,當我們意識到「有意義的巧合」,也就是對世界的主觀認知到,「一切存在形式之間的深刻和諧」。因此,這種奇蹟體驗,便會轉變為巨大的力量,給人超越理性的慰藉。
因此這部電影,令我不禁開始想:「究竟是電影詮釋了我的生活,還是我的生活詮釋了電影呢?」我想答案是,「生活即電影吧!」。於是我放下手中的三明治,走到陽台,也只有遠距上班,我才能在傍晚時分,遠離加班,欣賞夕陽照入家中的無敵美景。疫情下的儀式感,令人感到生命無常,卻也領略了無條件地受到寵愛。
延伸閱讀: 蔡雨杉「回收再利用(上)(下)」(引自《人間福報》)
https://www.merit-times.com/NewsPage.aspx?unid=389063
https://www.merit-times.com.tw/NewsPage2.aspx?unid=389206